历史的具象化
老文,一年前读梁永佳老师《地域的等级》的时候写的。
在《红楼梦》第五回中,宝玉进入秦可卿的房间午睡,曹雪芹对秦可卿房间的摆设有一段很有名的描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很多人认为这段描写在暗示着一些内容,这里不探讨这些。在暗示以上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描写呈现的是一个奢华的房间。显然,在一般人的眼中,武则天设立的宝镜比一般的宝镜具有更大的价值,金盘也因为飞燕起舞而更有价值,普通的木瓜只是水果,要真是伤了太真乳的木瓜,那可就是具有历史意义了。
而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马林诺斯基在看到库拉礼物的时候,想到了自己在爱丁堡参观皇家珠宝展的经历:“保管人告诉我们很多故事,这些珠宝是如何被这个国王或者那个王后在这样那样的场合佩戴的,其中一些如何被弄到了伦敦,引起了整个苏格兰强烈而正义的愤怒,它们又是如何被弄回来的,并且现在每个人应该如何高兴,因为它们被妥善地锁藏着,没有人能够碰到它们,所以是安全的。”马林诺斯基认为这些皇室珠宝,所谓的祖传遗物和库拉礼物一样,都是因为附着在它上面的历史情感才为人所珍爱。无论一件东西是多么的丑陋、无用,不值钱(比如木瓜),只要它在历史场景中出现并经历史人物之手传递,就一定会因此而成为传达重要情感联想的经久不衰的媒介,那么它也就为人们所珍爱。这算得上是对木瓜价值的最好注解了。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对马林诺斯基说:“每件第一流的臂镯和项链,都有其个人名字及历史;它们在大库拉圈内循环流通时,人们都知道它的名声,它们在某一地区一出现,就会造成轰动。”最一流的库拉礼物拥有故事,反过来说也对,只有拥有故事的库拉礼物才是最一流的库拉礼物。马林诺斯基在此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到底是因为某件库拉礼物是最一流的,才会拥有故事,还是反过来,是因为某件库拉礼物拥有故事,才成为了最一流的。对于马林诺斯基的研究来说,这并不重要。而在莫斯的《礼物》中,莫斯在引述库拉的资料时,特意强调了马林诺斯基研究中的“任何外罣,都有一个名字,有一种人格,有一段历史,甚至是一段传奇。”
对于那些有名的库拉礼物(或者叫外罣),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可以把它们的历史娓娓道来,他们很熟悉这些历史。在此我想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有名库拉礼物的价值来源于其历史;人们想要拥有一件库拉礼物的时候,不仅仅是想要物理的拥有这件库拉礼物,更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和历史产生某种联结。这一步迈得不大,也并不大胆。虽然有些跳跃,但是至少和马林诺斯基所述的“物体在历史场景中出现就成为了传达重要情感联想的媒介”相符合。这也和现代生活中的直观经验相吻合。
据说茅台酒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因为包装本身就较为简陋土气,而且又是陈列在农业馆,杂列在绵、麻、大豆、食油等产品中,根本一点也不起眼,所以最初无人问津。中国代表团怕茅台酒被埋没在农业馆,于是有代表提出将茅台酒移入食品加工馆陈列,以方便突出。搬动时,一位代表不慎失手,一瓶茅台酒从展架上掉下来摔碎了。陶罐一破,茅台酒酒香四溢。中国官员见此灵机一动,建议不必换馆陈列,只需取一瓶茅台酒,分置于数个空酒瓶中,并去掉盖子,敞开酒瓶口,旁边再放上几只酒杯。正好利用农展馆展品气味不浓,闲人不多的特点,任茅台酒挥洒香气,让参观者品尝。茅台酒敞开后酒香极为浓郁博览会会场里的参观者们纷纷寻香而来,争相倒酒品尝。农展馆里一时人头躜涌,热闹非凡,产生了轰动效应。最终获得金奖。这个故事流传甚广,茅台集团也没有忽略对此的推广。近些年来,对此故事也有一些异议,茅台则指责这样的异议是其他酒厂的抹黑。这事已然成为了一个罗生门,在此并不多行赘述,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茅台,还是其他酒厂,无疑意识到了历史的价值。茅台试图通过构建出茅台酒所在的历史场景,赋予茅台酒传奇性的方式,增加茅台酒与历史的联结,以此增加茅台酒的价值。而其他酒厂,或借鉴茅台的手法,增加自身与历史的联结,如汾酒翻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故纸堆,指出茅台所获的金质奖章是第三等的奖章,而汾酒获得的才是最高的奖章;或消解茅台酒的建构,宣称茅台酒考散发酒香吸引参观者的故事纯属杜撰。
或许不是历史在增进物品的价值,而是传奇。在玉石行业中,有这样一种戏谑的说法:“十玉八个是籽料,真不真主要看卖家的故事圆不圆润。”这种说法,显示出了,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具有更多故事的物件具有更多的价值。藏民天珠的售出也类似,每个购买天珠的游客都会听到关于天珠的传奇故事。
我们回到《地域的等级》这本书,这本书讲述了大理喜洲的本主崇拜文化。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以坐镇神都的“本主中的本主”段宗牓为例。段宗牓号称大理国之祖,是南诏丰佑的清平官和大将军,有除奸平夷,力扶幼主,远迎舍利。民间流传许多关于他的神话传说。他是大理地区最常见的本主,很多地区的本主都是段宗牓,但是这些本主并不相同。在神都,他是和其他神仙商议到白天只能留下其他神仙一起做本主的爱民皇帝;在中央祠,他是远征狮子国受伤,取代亚本主的中央皇帝;在马久邑南村,是和村姑偷情的本主。在本主崇拜中,爱民皇帝、中央皇帝和清平景帝并不是同一个本主,虽然他们都是段宗牓。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是不同的本主呢?
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侧面,首先,本主文化中并没有否认这些本主是同一个人;其次,虽然是同一个人,但并非是同一个本主。这不同于马尔斯和阿瑞斯,赫尔墨斯和墨丘利,阿芙洛狄忒和维纳斯的关系,这些是同一个神在不同的神话体系中不同的名字。而同人不同本主的现象,是出现在同一个信仰体系下的。
在希腊神话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
宝瓶座的形象是一个持着瓶子在斟酒的美少年加尼墨德,据说他是特洛伊的王子。有一天,他替父亲看羊时,宙斯在天空经过,一见加尼墨德即对他迷恋,宙斯变身成一只老鹰掳走加尼墨德到奥林匹斯山。宙斯对自己所变过的那只雄鹰也十分得意,就把它变作一个星座,这就是天鹰座。
传说腓尼基的女儿欧罗芭在海边戏水,被风流成性的主神宙斯看见,为了避开天后赫拉的眼目。宙斯化为一头健美的大白牛向她走去,当公主慢慢靠在牛的身上时,这只牛突然背起了公主朝着天空飞去。事后宙斯又恢复原形,将自己的化身大牛置于天上成为众星座之一。
金牛座和天鹰座,实际上都是宙斯。从这种角度来说,金牛座和天鹰座,大约都是宙斯座,是相同的。但是,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星座。虽然和本主文化一样,希腊神话没有否认金牛座和天鹰座都是宙斯,但是同样的,同一个神,却是不同名的星座。
那么,希腊神话与本主文化,和前面所述的“物体在历史场景中出现就成为了传达重要情感联想的媒介”,和“任何外罣,都有一个名字,有一种人格,有一段历史,甚至是一段传奇。”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要重新回到那句话:“每件第一流的臂镯和项链,都有其个人名字及历史;它们在大库拉圈内循环流通时,人们都知道它的名声,它们在某一地区一出现,就会造成轰动。”前面我们那个迈得不大也不大胆的步也可以这样表述:物品的价值来源于其与历史的联结。在这种跳跃中,我们似乎忽略了什么。在说物品的价值的时候,实际上忽略了,库拉礼物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并不被当做物品,至少对于那些有名的库拉礼物来说,他们被当做一段历史,一段传奇,他们是有名字的,是人格化的!
同样的,如果真的存在伤了太真乳的木瓜,这个木瓜并非是因为在历史场景中出现才成为了传达重要情感联想的媒介,也并非是和历史的联结,这个木瓜本身就被视为历史,木瓜的价值来源于凝结在其上的历史、传奇。这个木瓜被叫做“伤了太真乳的木瓜”,这一命名已经使得它脱离了普通的木瓜,他的价值和木瓜没有任何关系,即使这个木瓜实际上是“指爪”或者西瓜,也都无所谓。
而对于本主,使得他们成为本主,保佑佑下之民的,并不是段宗牓。而是为了降雨聚集神灵,结果商议到白天只能留下其他神仙一起做本主的爱民皇帝;是为了帮助缅甸抵御狮子国而受伤的中央皇帝;也是和本村村姑偷情而对本村格外照顾的本主。爱民皇帝,中央皇帝,清平景帝,都是将传说故事凝固下来,人格化的一段传奇的名字。希腊神话中,金牛座纪念的并不是幻化金牛的宙斯,而是宙斯幻化金牛带走欧罗芭,最终导致了欧罗巴大陆——欧洲出现的这段传奇。金牛座,具有一个名字,有一种人格,虽然没有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是有一段传奇。
将历史或传奇人格化,并非是本主文化与希腊神话独有的,在很多崇拜体系中都有类似的体现。
门神,作为民间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人们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避鬼卫家宅。门神有很多,郁垒神荼哼哈二将等都是传说中的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一对门神也为人们所熟知。《西游记》记载:泾河龙王触犯天条,由魏征处斩。泾河龙王托梦求救李世民,李世民为了不让魏征斩龙王,留魏征下棋。结果魏征下棋时睡着了,梦中斩龙王。泾河龙王怪罪李世民,夜夜纠缠不休。李世民让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在床前守卫,才得以安寝。后来秦叔宝与尉迟敬德手持兵刃的形象成为了民间的门神形象。龙王的纠缠被解决后,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已经不再护卫李世民床前。但是民间并没有因为秦叔宝尉迟敬德不再护卫李世民床前就停止将他俩作为门神。作为门神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是秦叔宝尉迟敬德护卫李世民床前阻挡泾河龙王纠缠这段传奇的人格化凝结。被崇拜的并非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两个人,而是人格化的传奇。
在寺庙中,神像往往具有不同的姿态,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以关帝庙为例,关公的塑像除了持刀肃立以外,也有单刀赴会,刮骨疗毒,夜读春秋等形象。被崇拜的,除了作为整体的关帝形象之外,也有被具象为不同形态的关公传奇。将神像塑造为不同的姿态,并非为了表现历史:在关帝庙中,不会出现败走麦城的关公塑像。这和前面所述的,增加价值的并非是历史而是传奇是一致的。虽然,人们往往会有意无意的忽略那些不那么传奇的历史,并把传奇当做历史本身——特别是把传奇作为崇拜的时候。
佛寺中也会有不同的佛祖法相与菩萨法相,佛祖可能会在舍身饲虎,割肉喂鹰,菩萨可能是神女,也可能在撒药。
人格化的传奇会成为人崇拜的内容,也可能会成为人追逐的内容。库拉礼物作为人格化的传奇,使得传奇具有了实体。马林诺斯基已经指出,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并不会和现代人一样用“价值”来衡量库拉礼物。任何一个岛民只能短暂的拥有某个有名的库拉礼物,而无法占有。那么这种追逐和现代人的价值衡量是否具有某种相似性呢?再次回到那句话:“每件第一流的臂镯和项链,都有其个人名字及历史;它们在大库拉圈内循环流通时,人们都知道它的名声,它们在某一地区一出现,就会造成轰动。”对于一个库拉礼物来说,它的历史是什么呢?是它被谁制造,被谁交换,被谁用了什么手段。也就是说,库拉礼物的历史,就是人们追逐他的历史。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们在追逐具有传奇的库拉礼物的同时,也在参与创造这种传奇的历史。通过这种追逐,人与历史相联结,个人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人通过对具有传奇历史物件的占有,也可以完成与历史的联结。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不仅喜欢占有传奇历史物件,也喜欢在这些物件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具体来说,就是盖章和题字。唐朝画家韩干的《照夜白图》被盖了五十多个印章,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只有二十八个字,乾隆在上面写了上万字的读后感。自诩千古一帝,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通过对历史物件的占有和留印记,完成了和历史的联结。
对传奇和历史的联结,通过与传奇和历史的凝结物联结进行。正如马林诺斯基所说,物体在历史场景中出现就成为了传达重要情感联想的媒介。物体在这里扮演了联结人与历史媒介的角色。对于人来说,历史附着在物体之上,物体就是历史本身。无论是占有,还是通过库拉交换进行追逐,都是进行联结的一种方式。
通过对人格化的传奇进行崇拜,举行仪式,个人也与这些传奇和历史进行了联结。而本主文化中,被人格化的传奇,都具有地域的属性。无论是中央皇帝,爱民皇帝还是清平景帝,都是对于当地社会来说的传奇。正如《地域的等级》这一标题所展示的,这种传奇可大可小,具有等级。然而,这些传奇,都直接的和当地的社区联系在一起。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宗教来源于社会。对本主的崇拜显然和社区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想要指出的是,通过将社会的传奇与历史具象化,并对这一具象进行崇拜的方式,人与社会获得联结。这并非是大理地区特有的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地方表现的形式不同。这种具象,可以是历史和传奇附着在物件上,也可以是历史和传奇被人格化。
本作品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 进行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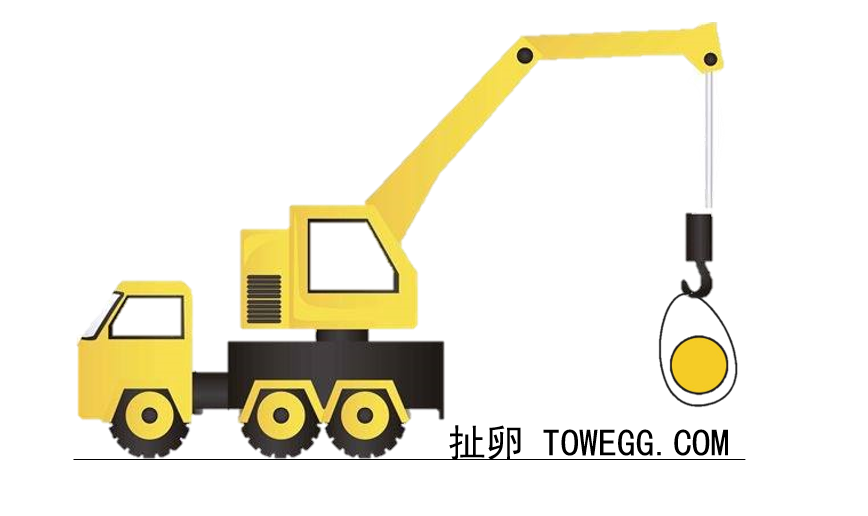 扯卵
扯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