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网络的民族志而非网络民族志
本文原为我硕士毕业论文的“方法论讨论”一节,去除和原文田野密切相关的内容之后发出。
(一)参与观察与文化相对主义
博厄斯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写道:“要求被研究者不收我们的文化为基础的任何评价的束缚。只有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能深入每种文化,只有深入研究每个民族的思想,并把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的总的客观研究的范围,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 [1]博厄斯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强调的是所谓原始人与文明人的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然而在应用文化相对主义这一人类学研究基本立场时,往往忽略了对现代文明的适用。当我们在研究现代人与现代文化的时候,似乎可以把一切罪恶的根源推到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上。
当下一些对汉服群体的研究,往往和亚文化研究一样,虽然对亚文化群体不乏关怀之意,但是这种关怀仍旧看起来像是高高在上的悲悯。这些研究将亚文化群体和其文化本身,作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无法否认,这种研究是具有人文关怀的,但是,这种关怀似乎也隐含着一些歧视和排斥。而另外那些由爱好者本身进行的研究,则在为汉服辩护,努力论证汉服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而其最终的落脚点往往落在如何更好的宣传汉服和发展汉服上。所以我将努力秉持着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一当代的群体,不为他们辩护,也不把他们作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或许可以引用格尔茨所说的,人类学不研究村落,只在村落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在汉服群体里做研究,而非研究汉服群体。我试图像进入一个社区一样进入汉服群体,所以我在进入的时候不掩藏自己的目的,不假装自己是个汉服新人,而是直接和我接触的人说明我的研究者身份。同时,我在研究的时候注重汉服爱好者们的日常生活,对很多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尝试由熟转生;同时,在调查期间也注意不要只关注与汉服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内容。丹尼尔米勒在他那本《脸书故事》里试图论证“如果库拉圈证明了人类学家对于‘文化’一词的意义,那么脸书也同样如此”,也就是互联网的文化和库拉圈这样传统的人类学所研究的文化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我也试图把汉服爱好者群体当做异文化来研究,把他们(以及“我”)置于他者地位,这就会对一些很平常的事物由熟转生,记述一些可能我和他们以及本文的读者都已经司空见惯的琐碎日常。我希望用这样的做法,对当下网络民族志方法做出一些反思。
(二)使用网络的民族志
汉服群体缘起于网络,爱好者间的日常交流很多都在网上进行,再加上2021年新冠疫情仍旧存在,线下的群体活动减少,所以网络民族志这一方法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我的主要方法。郭建斌和张薇提出,和传统的“民族志”相比,“网络民族志”只是对象和具体的操作策略存在差异,在方法论无根本性变化.[2]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是否存在本质差别,这个问题贯穿着网络民族志理论讨论的始终。学者们使用“网络民族志”、“虚拟民族志”和“数码民族志”等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回答。
库兹奈特将网络民族志定义为“利用互联网来研究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同时认为网络民族志可以和传统的民族志相结合,共同研究与互联网相关的文化现象。[3]而海音用虚拟民族志一词,同时使用 “虚拟”和“民族志”来强调,使用民族志方法对“虚拟”世界进行研究的可行性。虚拟世界并不虚幻,而是真实的、物质的、文化的。[4]这二者都强调不能够割裂线下和线上空间。而海音则进一步地强调线上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体性,弱化线上与线下空间的对立,强调“民族志”的意义。[5]研究者围绕所研究的互联网文化社群使用各种研究手段进行研究,这种文化的意义、符号系统、价值、话语、社会关系等并只存在于互联网上。而丹尼尔米勒在《数码人类学》一书中则提出,数码人类学并不会让非数码世界显得非中介与无视框,[6]也强调数码世界和非数码世界没有本质差异。[7]
虽然从理论构建上,“网络民族志”、“虚拟民族志”和“数码民族志”三个脉络都强调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可割裂性,但是他们仍旧将研究对象限于和互联网相关的社群或者文化。然而,在互联网越来越融入日常生活的当代,几乎任何社群和文化都可以说和互联网相关。孙信茹在对大羊普米族村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期间,被邀请加入了村民建立的“大羊青年”微信群,开始运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研究。[8]如果将使用网络交流平台的群体都定义为和互联网相关的社群,那么大羊青年微信群无疑符合这一定义。但是这样的话也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在现在这个时代,到底还有多少群体不和互联网相关呢?在我看来,网络生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网络民族志只是对这一部分的考察。线上和线下的生活呈现一种互嵌的形态,无法分割,有时甚至无法区分。
这种互嵌带来的,或许是网络民族志和传统民族志的无法分割。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部分:网络民族志是只观察网上吗?线下的民族志就不关注网络了吗?从理论上讲,显然第一个问题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网络民族志的理论都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强调这一点。而第二个问题上,并没有人明确的反对在民族志中关注线上生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民族志调查常常忽视了调查对象的线上生活;同时,线上生活得到关注时,研究者往往声称使用了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而使用网络民族志调查的研究者,更是常常忽略了调查对象日常生活的非网络部分。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线上和线下社会网络的融合,描述了这一线下,却常常缺失对线下部分的参与观察。高崇在对SZ人在北京QQ群的网络民族志调查中,指出“线下交往也越多,同时线下交往反过来促进线上互动。”[9]他记述了这个QQ群内可以临时发起聚会,也会提前筹划组织聚会,但是,却缺乏对线下聚会的呈现。 无论他是否参与了这些线下的交流,在他的文本中,线下的部分都是缺位的。高崇至少已经意识到了线上和线下的交融,而更多的研究者,甚至忽略了线下的存在。
这并非是网络民族志独有的问题。庄孔韶就曾强调在民族志研究中,问题研究不是就事论事,需要避免只关心和问题直接相关的要素,忽视对间接相关问题的关注。[10]这其实就是网络民族志研究忽视了线下生活的本质原因。当下使用网络民族志方法的人,往往是在研究某个具体的网络现象或文化,而对这种问题的关心,有时会忽略了其他因素。这或许也是因为人类学的方法论被各学科广泛引入之后,参与观察的方法被一些研究者理解成了民族志方法论的全部。就像林开世所述“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大部分內容,其實是無法用‘研究方法’來形容。在田野中,我們做很多事,其中包括根據某些研究旨趣來收集所謂的‘民族誌資料’,但是更多時候,我們就是‘做’。‘做’指的就是‘做人’、‘做事’、建立關係、交朋友等等。” [11]而将人类学民族志狭义的理解为参与观察的这些研究,忽略了参与互联网现象或文化的具体的人,也就是忽略了这些具体的人的日常实践和他们之间的日常交流——这种忽视不分线上和线下,只是取决于和研究问题的直接相关程度。
在我看来,网络民族志和民族志之间已经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民族志这一名词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只是在民族志研究时使用了网络。[12]在村落里做田野的人类学家经常去村口戏台和村民聊天,是不会有人把这叫做戏台民族志的,只能说,我在村里做田野,我经常去戏台。就像赫兹菲尔德呼吁用人类学在城市和乡村的提法代替都市人类学和乡村人类学的学科划分[13],我的田野实践也是在呼吁用“使用网络的民族志”代替网络民族志。而本研究,就只是在做民族志研究,使用了网络。
(三)新的伦理问题
上一节的讨论在强调线上与线下空间的互嵌,是在强调线上和线下的不可分割,但是并不否认线上的部分具有独特的问题。即使按照我的说法,在做民族志研究时使用了网络,那么这种方法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按照人类学的惯例,报道人的名字需要做匿名处理,在一些作品中,连田野点的位置都作处理。而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中,一部分研究直接使用网名,甚至有人在做微博相关的内容时,直接截图微博内容。似乎可以辩解说,网名不是被研究者的真名,本身就是匿名。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如此。对报道人的名字做匿名处理,不是为了隐去他的真名,而是为了保护报道人。在我的田野中,有些报道人的网名已经用了快二十年没换过,对于他来说,这个网名的意义就是真名,不能作为匿名。而将田野点的位置做模糊处理,但是对我来说要做的更多。去掉地理信息对某个具体的田野点来说,其实并不难,但将田野点模糊处理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报道人,是为了防止通过地点等信息使得报道人被曝光。
也有人辩解说,微博作为微型博客,本身就属于公开平台。虽然微博在设计上的确属于公开的平台,但是用户在上面分享的事物并非全都具有公开性,微博具有访问权限、圈子等一系列不同的设置,无法简单的视为公开信息。我在处理时采取了另外一种路径。首先,所有仅发表在不可以被公开搜索的平台(如微信朋友圈)的信息被视为私密信息,使用需要先征得作者同意。而发表在可以被公开搜索的平台的信息,只有那些表露出公开意愿的信息可以直接使用。我将具有标题、作者署名、日期,符合公开发表格式的博文视为公开意愿的表述。信息声明支持知识共享署名相关国际许可协议,或者有诸如欢迎转载之类的内容,也视为具有公开意愿。
在我硕士论文中涉及的人物都进行了匿名处理,不仅不是真名,也不是网名。同时,一些报道人的线下生活部分(比如工作学习单位)都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一些事件的发生顺序等细节进行了些许调整(调整顺序的事件没有因果关系),一些多人事迹被整合在某个角色身上,而某些个人的事迹被拆分为多个角色。只有一些同袍以论文、倡议书、公开演讲、媒体报道等形式发布的言论,其署名仍保留。其中涉及的地名和组织名也都是假名。除了诸如西塘汉服节和福建礼乐大会这样规模太大以至于匿名没有意义的情况。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DANIEL M. 脸书故事[M]. 段采薏, 丁依然, 董晨宇,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2 郭建斌, 张薇. “民族志” 与 “网络民族志”: 变与不变[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5.
3 库兹奈特. 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 : 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M]. 叶韦明, 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4 HINE C.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s a middle range methodology for contemporary STS[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07, 32(6): 652-671.
5 曹晋, 孔宇, 徐璐. 互联网民族志: 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研究[J]. 新闻大学, 2018(2): 18-27.
6 无视框,指没有视框,视框在此处指数码世界的屏幕具有的边框。
7 丹尼尔・米勒,等. 数码人类学[M]. 王心远,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8 孙信茹. 线上和线下: 网络民族志的方法, 实践及叙述[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11): 34-48.
9 高崇, 杨伯溆. 新生代农民工的同乡社会网络特征分析——基于 “SZ 人在北京” QQ 群组的虚拟民族志 研究[J]. 青年研究, 2013(4): 28-39.
10 庄孔韶. 人类学概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12-116.
11 林開世. 什麼是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 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J]. 考古人類學刊, 2016(84): 77-109.
12 这并非是说当下网络和非网络的区分已经完全没有了意义,网络民族志的对象和依托网络进行的田野调查具体的操作策略的确和非网络有着不同。但因此认为网络民族志与民族志截然不同则并不妥当,他们的方法论并没有根本性差异
13 Michael Herzfeld. 都市中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和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Modo 人类学讲习堂第 64 场,2020. 在这一讲座中,Herzfeld 认为,尽管都市较乡村有一系列新特征,如地域广阔、人群流动、阶级分化,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都市人类学与乡村人类学的分野,他更愿意使用人类学在城市和乡村的提法,而不是都市人类学和乡村人类学的学科划分。
本作品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 进行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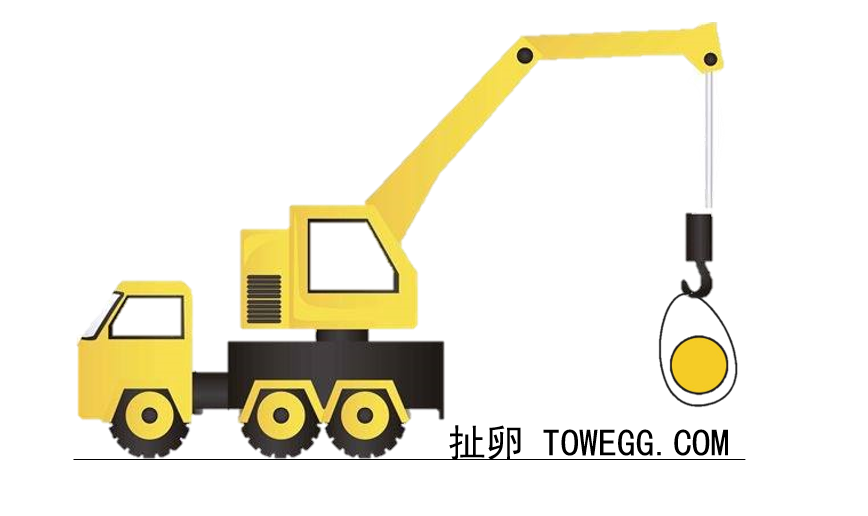 扯卵
扯卵